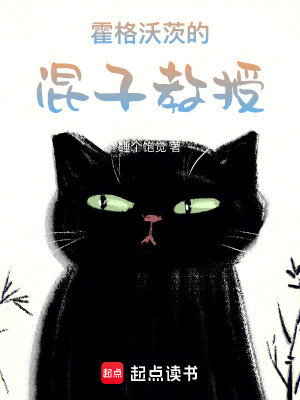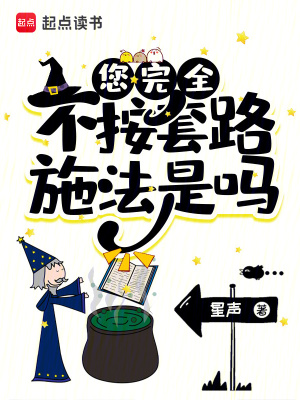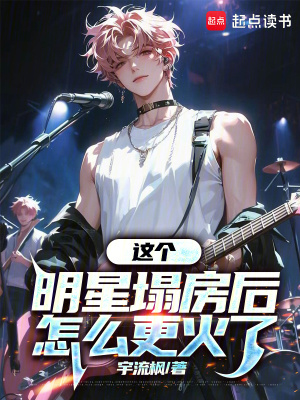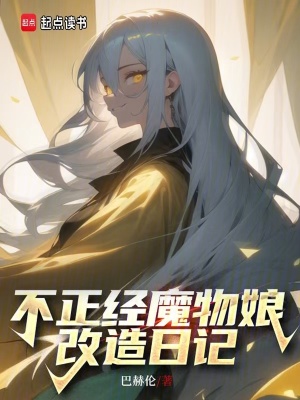出行凭证得申报理由。
城门处,一个军士正查验一群男子的出行凭证。
“游学?”
军士抬头,四十出头的男子撩起垂落在脸颊那里的一缕长发,“看清楚,长脸。”
“四十多岁还游学?”一个年轻军士嘀咕,边上的老卒踹了他一脚,低骂道:“花魁大赛有诗会。”
男子挑眉,“正是。”
蒋庆之觉得花魁大赛单调了些,便同步举办了一个诗会。
诗会的评委竟然是名妓团,这个消息散播出去,那些自矜身份,想来‘观摩考察’花魁大赛的老蛇皮们顿时就乐了。
诗会?
吟诗作词我擅长啊!
于是来松江府的人愈发多了。
等这批人进城后,年轻军士纳闷的道:“这些人看着大腹便便的,不像是文采了得的吧?”
老卒嘿嘿一笑,“吟诗作词的活大伙儿都会。”
“你会?”年轻军士知晓老卒只认识自己的名字,以及上官的名字,所以笑道:“有本事你便作一首,决赛那日我便代替你值守。”
“听好。”
“嗯!”
“一啊摸,摸到了……”
对于男人来说,吟诗作词只是一种消遣,也是一种装比的手段。
城中的逆旅尽数客满,陈连为此焦头烂额,便再度来请见蒋庆之。
“伯爷,不能再来人了。”陈连苦笑,“城中的青楼都住满了。”
青楼可以留宿,但价格很感人。
蒋庆之叹道:“人要活。”
“还请伯爷指点。”陈连觉得自己已经想尽了法子。
蒋庆之吸了口药烟,指指外面,“城中多少人家?挑选出一些和善的人家,令人上门交代规矩……随后把那些外来人安置在这些人家中。一日住宿多少钱,若是加上吃喝多少钱……”
“咦!”陈连一怔,蒋庆之叹息,“如此,那些人有了安置的地儿,不至于到处游荡。其次,百姓也有了收益,这是什么?双赢!”
“妙啊!”陈连一拍脑门,“下官怎地就没想到呢?”
因为这是民宿啊!
几百年后才有的东西。
“记住,为官者当把治下百姓放在心中。若是你把他们放在心中,这主意便会源源不绝……”
陈连拱手,由衷道:“下官谨受教。”
陈连急匆匆走了,蒋庆之回身,宁玉就在不远处,福身,“奴冒昧,方才听了伯爷一番话,奴便在想,为官者不该先效忠陛下吗?”
“陛下为何?帝王为何?”蒋庆之抖抖烟灰,“这个天下有生民亿兆,化为一便是帝王。”
“帝王是万民的代表?”
“嗯!”蒋庆之点头,“所谓效忠帝王,实则便是效忠万民,效忠这个天下。有人把效忠看做是个人升迁、谋取荣华富贵的工具,于是便把效忠的对象变成了个人。”
宁玉微微垂眸,“帝王便是万民的代表,帝王当如何统御百官?为官之道为何?”
“你这个问题倒是有趣。”蒋庆之笑了笑,“帝王乃是万民代表,统御百官,统御朝政的出发点,就应当是万民利益。帝王高居庙堂,根据当下万民之所求,万民之困境而做出相应的谋划,并督促百官施行,这便是帝王之道。至于为官之道……”
蒋庆之缓缓踱步,“人皆有私心,这不可泯灭……”
“长威伯,大公无私!”
这里是驻地前院,不知何时,徐渭等人都来了。
开口的是风尘仆仆的魏国公徐承宗。
“来了?”
“来了。”
徐承宗没说为何来,蒋庆之也不问,他继续说:“没有所谓的大公,人活着便有私心,就得有目的和追求。不同的是,有的人追求的东西于万民有益,便被称之为圣人。所以,从无所谓的大公无私。至于为官之道……”
蒋庆之沉吟着,一个官员进来,低声想和徐承宗说话,徐承宗摆摆手,示意稍等。他目光炯炯的盯着蒋庆之,低声道:“先前那番帝王之道,若是传出去,多少人会恍然大悟。”
这位……不愧是墨家巨子!
徐承宗此刻只想听听蒋庆之口中的为官之道。
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朝成名天下知。每个官吏都有着自己的追求,有着自己的目标。有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,于是便兢兢业业,勤勉为民……有的人只想着荣华富贵,只想着寒窗苦读多年,一朝出头,就该享受权力带来的甘美和各等好处……林林总总,龙生九子尚且子子不同,何况人。”
人是最复杂的动物,蒋庆之说:“有人说当教化,教诲官吏,在我看来,教化是一回事,最要紧的还是监督。”
为官之道,怎地变成了监督官员之道?
众人不解。
“让那些官吏不敢贪,不能贪。”蒋庆之见众人不解,笑道:“所谓为官之道,有些大而化之。说实话,人性本私,刚出仕时的官员,大多都有崇高的追求,可在宦海中为何变了?环境!”
蒋庆之想到了陈连,“那些奸臣佞臣,哪怕是秦桧,出仕时也曾满腔热血,一心为民。为何变了?”
“是这里。”蒋庆之指指周边,“宦海就是个大染缸,或是说,人间就是个大染缸,一个白生生的人跳进来,要么被染成一种颜色,要么便会被排挤。被排挤的郁郁不得志,无法出头。选择和光同尘的,渐渐沉迷于名利欲望之中。”
徐承宗说:“长威伯的意思,宦海无好人?”
“人性有善恶,不能一概而论。”蒋庆之说:“就说外界口中的奸佞严嵩,当初也曾豪情满怀,为何变成这等模样……”
徐渭说:“这便是伯爷说的跳进了大染缸中,他挣扎了一番后,最终选择了和光同尘,被染成了一个颜色。”
他明白了。
徐承宗也明白了。
宁玉等人也明白了。
“没有什么为官之道。上位者与其奢求官员们能恪守君子之道,不如用制度去监督他们,督促他们。所谓的为官之道,不是个人之道,而是……制度之道。”
“用制度来让官员们遵循的道,便是为官之道。”宁玉低声说,她低着头,眸子里有异彩,也有复杂的情绪。
儒家多年来追求的便是君子之道,文章诗词,无不遵循这等准则。
在儒家的眼中,只要读了圣贤书,只要遵循圣贤的言论去做人,做事,那么此人便是君子。
今日蒋庆之一番话,却从人性的角度彻底颠覆了这个理论。
——人,皆有私心。不可能成为儒家口中的那等君子。
与其奢求他们变成君子,不如琢磨如何用制度,用规矩来让他们成为君子。
也就是说,靠自觉,是靠不住的。
唯有举着棍子,拿着胡萝卜,才是统御百官之道。
“这是帝王之学!”门外有人惊呼,随即人影一闪,一个老头儿冲了进来,目光转动盯着众人,“今日长威伯这番话,你等最好守口如瓶!”
宁玉一怔,心想这位是谁,口气大的不行。
徐承宗见到老头儿,身体一震,拱手,“陈公不是致仕归乡了吗?怎地来了松江府?”
老头儿并未回答他,而是目光炯炯的看着蒋庆之,“可是长威伯?”
蒋庆之点头,老头儿拱手,“老夫陈铮。”
蒋庆之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,徐渭却讶然,一边冲着陈铮拱手,一边低声道:“伯爷,这位乃是当年陛下的先生,曾辅佐陛下多年,多年前致仕归家,本以为……谁曾想竟还活着。”
帝师?
蒋庆之突然想起来了,当初曾夏言曾提及过此人。
——陈铮此人乃大才,陛下在潜邸时,此人曾教了陛下五年。陛下入京,陈铮本想辞别,是太后出面挽留了他。
陈铮跟随着道爷入京,杨廷和与张太后联手压制道爷,道爷奋起反击,当时他身边的第一谋士便是这位帝师。
夏言曾自嘲说,若是陈铮在,也轮不到自己做首辅。
杨廷和黯然下野,所有人都觉得陈铮会入阁,混几年资历后便能接任首辅。谁曾想这位老先生却不肯,一直想回乡。
——富贵于我如浮云!
这位帝师辅佐道爷成功逆袭后,便想功成身退。道爷自然不肯放人。可没几年,不知是真不习惯官场,还是什么原因,陈铮一病不起,只求死在家中。
道爷没办法,只好放人。
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应当是在家中等死,可此刻的陈铮看着精神矍铄,脚下生风……
比老夏言都精神。
这位的资历之深厚,嘉靖朝无人能及。
蒋庆之拱手,“见过陈公。”
陈铮颔首,围着蒋庆之走了几圈。他背着手,嘴里喃喃有词,止步道:“你方才那番为君之道,可曾教授给那两个小子?”
两位皇子在他的口中变成了小子,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。
蒋庆之摇头。
“为何?”陈铮问道。
“他们这个年纪不懂这些,太过形而上和大而化之,只会带偏他们的想法。”蒋庆之说:“因材施教,不可拔苗组长……”
“有意思。”陈铮点头,“老夫本在家等死,可陛下三番五次想让老夫重返京师。老夫不肯,陛下便令人传话,说有个有趣的年轻人,比之当年的老夫更有趣。陛下说……老夫一直未曾寻到衣钵传人,此人,正适合!”
意思。”
这可是帝师啊!
若是能拜他为师,我滴神,那就是道爷的师弟。
在艳羡的目光中,蒋庆之笑了笑。
“我从未有拜师的想法。”